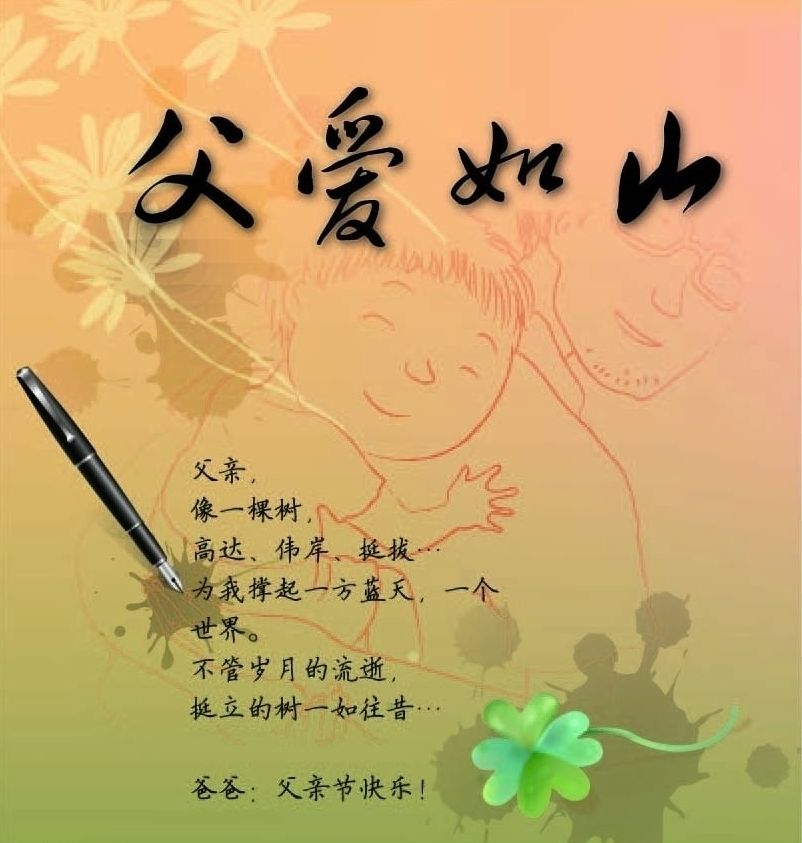
小时候,父亲是高大的像一座山,给我们最坚实的依靠。他总用他那伟岸的身躯艰辛、倔强、坚韧地撑起一个安祥、温馨的家,流露在我们面前的总是慈祥的微笑,教会我们的是诸多人间高尚的品质,让我们兄妹、姐弟在这个温馨的家中简单、快乐、幸福地成长。父亲是一位不善言谈的人,但父亲非常宠爱我这个家里唯一的女儿。
一次,买来他最爱吃的炉果和老式面包,走到父亲家的楼下。我看到父亲拄着拐杖,驼着背,一步一挪地向我走来,我的心在隐隐作痛,眼泪瞬间模糊了眼睛。我突然感到父亲老了。这身影仿佛牵动着我的思绪。近八十年的风风雨雨,已经抹去父亲年轻时所有的俊朗,如今已弓腰驼背,稀疏而凌乱的白发,饱经风霜的脸庞留下一道一道沟壑般的波纹,仿佛承载着岁月的沧桑往事……
听母亲说,解放前,祖父、祖母带着父亲去外乡讨饭,住无片瓦,立无寸地,那种凄凉和苦难是我们后辈所无法想象的。解放后,1955年父亲从老家河南应征入伍。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。在部队学习了文化,并学会了开汽车。1958年跟随王震将军的十万官兵来到北大荒。当时的北大荒,夏天蚊虫叮咬,冬天西北风、白毛风刮在脸上,就象刀割一样,晚上穿着皮袄,戴着狗皮帽睡觉,早上起来眉毛、眼睛全是冻霜。手冻裂,脚冻肿是常事。住的是“地窨子”。工作从开垦荒源到修建铁路、修建公路。后来到了虎林酱菜厂当了一名工人。
由于家庭人口多,我们家有四个孩子,三男一女,我排行老二。奶奶与我们一起生活。在那商品、粮食奇缺的年代,靠父母那点为微薄的工资养活着一家七口人,常常是不到月底就没了钱和粮食。父亲到酱菜厂上班,就是为了能养两头猪,到年底卖猪换点钱和粮食以贴补家用。
从我记事起,就记的父亲上班时挑着两个空土筐,下班时一个筐装满豆腐渣、另一个筐装满酱渣,筐底下还淌着水,父亲从离家3公里的工厂挑回。每次回家都是汗流浃背。每当这时,妈妈就会迎上去,接过父亲手里的扁担,让父亲休息。奶奶抓一把豆腐渣闻一闻,如果没有酸味,就炒一盘当菜吃。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挑回的是工厂做豆制品的废料,工厂1角钱一挑卖给工人回家喂猪的。那时的糕点可是稀罕之物,家里有时也买点“光头饼”、“大饼”之类比较便宜的糕点,可那是给奶奶吃的,父亲用一个小篮装着,挂在房梁上,小孩是够不着的。奶奶有时悄悄的分给我们吃点。那时的我比筐高不了多少,我常想我要是能挑起一挑东西就好了。到了八十年代,哥哥当兵,我招干参加了工作,家里的经济状况有了好转,九十年代初小弟考上了湖南大学,退了休的父亲为了不牵扯我和哥哥,用自行车从原单位批发酱油、醋往小卖店送,好多挣点钱供小弟上大学。父亲的腰就是这样一天比一天弯的厉害。现在,我们四个孩子都成家立业,日子过的都不错。哥哥、弟弟经常回家探望父母。十年前儿女集资为父母买了楼房。直到现在父亲还自已种点了“自留地”,每到收获的季节,我们餐桌上就会品尝到父亲亲手种植的没有农药,没有化肥的“绿色蔬菜”。
父亲出身贫寒,一生辛劳,却从不抱怨,只是安分的耕耘着自已劳碌的一生,默默地让岁月在脸上刻划着一生的艰苦历程。没有华丽的词语,没有亲昵的做作,父亲的爱是沉甸甸的,不会直接表达,但父爱在我心中印得最深,时效最长,感受最涩,受益最大。父亲的爱如大山一样高大而耸立,做儿女的永远在山的庇护下,幸福的生活。
如果说母爱如水,那么父爱是山,如果说母爱是涓涓小溪,那么父爱就是滚滚激流,父亲的爱每一点每滴都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,父爱和母爱一样,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。